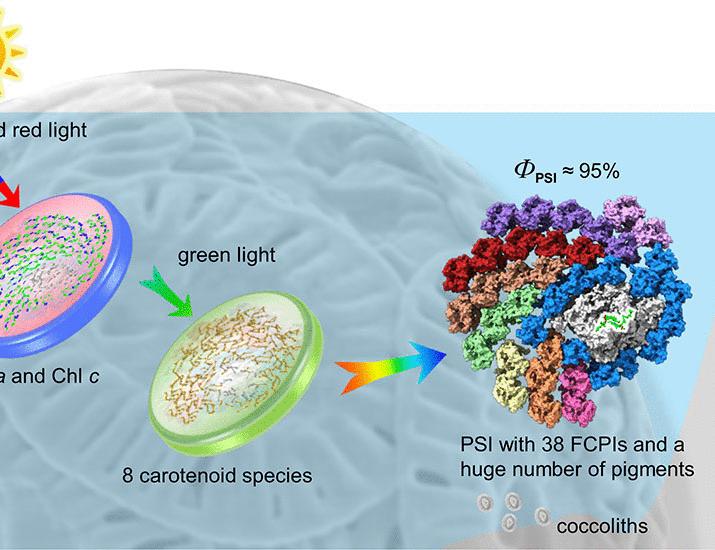2个月前得知Ozzy要来这个城市演出的消息时我很吃惊,虽然我在下城也看到过零星的几家摇滚文化店,总觉得这个地方的重金属乐迷不会太多。再说了,该有多老才能当上Ozzy的乐迷呢?这个老家伙的唱片公司甚至隔上个几年把黑色安息日的老曲子编排一下出个精选集,或者找新的乐手给Ozzy配乐混编一下就能随便卖出几百张专辑了。今晚距上一次Ozzy携黑色安息日原班人马来维多利亚已经将近30年了,我没想到现场会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这也间接说明自由开放社会下的文化会更加多元吧?我开始听重金属的时候,朋克刚刚终结了一个“快乐得没心没肺”的金属时代,摇滚界发出“金属已死”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摇滚乐就跟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思潮一样,完全没有隔代这一说,现代后现代思潮是同时进入中国,我们也是摇滚后摇一起听大的(所以我老板听说我也喜欢The Who的时候很奇怪)。
年过六旬的老Ozzy唱了将近2个小时,另一个能连续又蹦又唱这么长时间的老家伙我目前只能想到Iggy Pop。但返场之前的最后一首歌Crazy Train的时候老家伙唱到高音一下子唱劈叉了,赶忙把话筒伸向了观众,反正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虽然掩过去了,但我在那一刻突然为这个当年的“黑暗王子”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难过。其实整场演出感动我的镜头还是不少的嘛,比如那些虔诚的小伙子们,我想他们的心情就跟我当年第一次听崔健现场时差不多吧;再比如唱“Dreamer”时满场的打火机。我还终于明白了混rockbbs的时候我们版的版主喜欢形容“军鼓声打得像炮弹一样”的感觉了。还有,这个老家伙保持了朝观众泼水的传统,但比起水桶,他显然更喜欢直接用高压水喉了……而且,而且水好像还是带白色颜料的。没借相机过去真是失策了。
我会唱的几首基本上全唱了,“Paranoid”, “Shot in the Dark”, “No More Tears”, “Crazy Train”, “Mr. Crowley”, 而且返场的时候竟然唱的是我最喜欢的这首Mama, I'm Coming Home,没唱“Goodbye to Romance”有点遗憾,但运气已经好得不像话了。当唱到“我已千万次注视过你的面庞,当我们彼此分离,我不在乎阳光雨露”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我扭过头就能吻到你的脸。
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维多利亚听乐记
维多利亚国际爵士音乐节是我在国外参加的第二个音乐节。据官网上的消息,为期十天的音乐节来了350多名艺人,13个舞台上演了90多场演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听说过的只有乔治本森(弹吉他的都应该有所耳闻),美国爵士吉他三巨头其中的两位John Scofield和Bill Frisell,以及08年去过在中山音乐堂举办的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的Mike Stern(那年的阵容异常强大,John Scofield也参加了)。其余的都没听过但应该还有不少牛人,也许我对不上是谁,也许不是吉他手所以不知道。当然想听这些牛逼闪闪的人弹琴是要掏不少银子的,乔治本森在Royal Theatre为本届音乐会开了场,门票抵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十三个舞台里只有一个露天的Centennial Squre免费,让我这样的穷人也可以欢乐一把。
百年广场作为新人试炼场也有几场我钟爱的演出,另外还有一场听得我肝胆俱裂的(这事儿得问陈瑛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纯爵士音乐节,跟国内的不大一样。在国内我只知道北京的“九门”和上海国际爵士音乐节近几年有高水平国外艺人来助阵,参演的国内乐队基本上拿得出手的爵士乐手依然是从上个世纪末就数得过来的那么几个,剩下的就是摇滚乐手来掺和掺和。除此之外我还发现自从国内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开始遍地开花之后不管啥演出,名单上怎么翻来覆去都是同一批摇滚乐手的名字捏?而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自打开放就是本土爵士乐仅有的阵地。三十年过去了,这种音乐形式甚至比摇滚乐还难以在中国发展。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爵士乐就跟“可口可乐”一同来到了中国的上海,跟周立波眼里的咖啡一样被贴上了“小资”的标签,霞飞路的百乐门里紫醉金迷的生活恐怕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领略一番了。说句题外的,周老师傻就傻在觉得上海就是品味,就小资,以为这些气质从来都是上海气质的一部分。比如像旗袍这样的东西,其实说到底跟爵士乐一样都是外来的,只不过时间长了,旗袍就莫名其妙变成中国的“传统服饰”了。从老上海留下的纪录片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爵士乐正赶上摇摆乐(Swing)的时代,而爵士乐史上的第一个Legen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则扮演了传教士的角色,是他把摇摆爵士从芝加哥带到了纽约。纽约今天成为爵士乐的中心,他起了一定作用的。另外,老上海的爵士乐也仅限于歌舞厅,跟摇滚乐在八十年代刚到中国时的的遭遇相似,爵士乐也被国民政府当做是靡靡之音。
但相比较摇滚乐,爵士乐在中国难以发展的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爵士乐的传统和渊源很厚重。这种脱胎于布鲁斯的音乐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了,但布鲁斯又继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存在,继续影响着爵士乐和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摇滚乐。爵士乐刚传到老上海的时候,Ragtime的黄金时段已经结束了,但跟Ragtime一样,爵士乐也是作为给白人伴奏的舞曲出现的。但因为一战让美国大发了一笔战争财,爵士乐的诞生地新奥尔良有大量有才华的黑人乐手都跑到北方的大城市里赚钱了。跟早年杀到北京树村里的摇滚小青年们一样,这帮穷得丁零当啷响的黑哥们儿白天给各种饭店啊咖啡座啊刷盘子碗,晚上到舞厅里演奏爵士乐好让白人跳舞,于是芝加哥成了爵士乐新的中心。
但跟北京的摇滚小青年不一样的是,这帮黑哥们儿玩儿起乐器都是真功夫,哪里是只需要三和弦和荷尔蒙的朋克能比得了的,这是爵士乐在国内发展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摇滚自打娘胎里就是叛逆的产物,从嬉皮士运动和垮派作家的“嚎叫”中就能看出它的所有标签:离经叛道,蔑视传统,向往自由。这简直就是为文革后压抑中的青年们量身定做的,虽然摇滚乐一直被挤兑,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摇滚乐已经不完全属于地下亚文化了。开放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摇滚乐,走向大众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参演草莓和摩登天空音乐节的艺人名单来看,摇滚乐已经偏向流行,而只有流行才能商业化。在国外从来就没有真摇伪摇之争,因为摇滚乐在这里是大众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阻碍爵士乐传播的这第二个音乐在事实上使我们仅有的爵士音乐家们存活了下来。付不起房租又录不出唱片的树村青年们只能滚蛋回家,而刘元,刘玥这帮技术上牛逼闪闪的音乐家随便给人家上上课也能糊口了。
闲淡少扯,上图。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这是一号出场的第一支乐队Sara Marreiros,主唱的父亲是葡萄牙人,融合了南欧拉丁风的爵士乐是我的大爱。最左边是意大利乐器曼陀铃,那个小提琴手是现场认识的,也就是当天第二支乐队的小提琴手。即兴布吉乌吉(Boogie Woogie)的时代就成了爵士乐的一部分了。从最初的阿姆斯特朗到Bepop时代的查理帕克又到后来冷爵士时代的Miles Davis,Themonius Monk,哪个不是即兴大师。
这是二号下午第二支乐队Nick La Riviere,我第一次看到正式演出吹奏海螺,因为音准无法精确控制,这哥们儿用手放进放出来调整气柱的流畅度。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号作为领奏。早期的爵士乐是短号(后来很少用了,因为音域跟小号一样却不如小号富于变化就被取代了)领奏,长号只是在低音区用滑音跟短号做和弦上的呼应。钢琴因为搬运太困难,早期很少用。左二是弦贝斯(很多很多人说这是大提琴,不是的),与电贝司一样负责低音的演奏。早期由于录音设备没法对弦贝斯拾音,低音都是用大号来演奏。(也叫抱号,还记得七八年前张老师跟我讲,因为太大了要抱着吹,所以叫抱号,哈哈)最右边是两个小提琴,取代了原来铜管和木管乐器作为主角时代的的黑管儿。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三号的第三支乐队Soul Shaker,吉他手看起来范儿太正了。曲风偏向R&B(以为周杰伦是R&B的请掉头)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这是本届音乐节最后一支热辣火爆的高中生乐队,听介绍感觉像张帆搞得那种学校,人数很多,学生们轮番上阵。左一是低音萨克斯,左二左三是中音和次中音,被挡住的是小号,三个合音后面还有电吉他和电贝司,中间是爵士鼓。从一开始,大乐团就是爵士乐除了伴舞的舞曲之外的又一个特征。但电视发明之后这个玩意儿是如此新奇以至于人们不再热衷于晚上去舞厅了,一个标准的16人的大乐团要巡演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只好走向小型化。
在华语流行音乐界第一次出现合音到前台上伴舞的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高凌风带着他的御用合音“阿珠”和“阿花”激情演绎“冬天里的一把火”(没错,这不是费翔的歌),之后此举风靡台湾,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学国外的,知道了任贤齐刘若英等等台湾艺人全是扒日本的,王菲扒的是卡百利。在闭塞的年代里,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谁叫我们“与人斗其乐无穷”来着。
看看这些孩子吧,他们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里,女孩子们都水灵粉嫩的,有一个合音还戴着牙套呢,可爱死了。我们那么大的时候又在干嘛。中国的中小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像民工,因为具有流动的特点——你毕业了就不再属于高中生这个弱势群体了,于是他们的声音就一直无法发出来,无人关注。所以韩寒有多牛逼,我最知道。同时一并感谢我音乐上的带路人张老师,你一定知道,高中时那段有音乐陪伴的日子,对我的人生是多么多么重要。
PS听到现场版的What'd I Say真是个惊喜啊,真希望能听到Ray Charles亲自唱这首歌,呵呵。最后这支乐队分明就是谁牛逼就翻唱谁的,还有Etta James若干首, Stevie Wonder的“Higher Ground”,“Signed, Sealed, Delivered”, Billie Holliday, 等等等等一堆后悔没背歌词的好歌。
July 6.2010
百年广场作为新人试炼场也有几场我钟爱的演出,另外还有一场听得我肝胆俱裂的(这事儿得问陈瑛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纯爵士音乐节,跟国内的不大一样。在国内我只知道北京的“九门”和上海国际爵士音乐节近几年有高水平国外艺人来助阵,参演的国内乐队基本上拿得出手的爵士乐手依然是从上个世纪末就数得过来的那么几个,剩下的就是摇滚乐手来掺和掺和。除此之外我还发现自从国内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开始遍地开花之后不管啥演出,名单上怎么翻来覆去都是同一批摇滚乐手的名字捏?而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自打开放就是本土爵士乐仅有的阵地。三十年过去了,这种音乐形式甚至比摇滚乐还难以在中国发展。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爵士乐就跟“可口可乐”一同来到了中国的上海,跟周立波眼里的咖啡一样被贴上了“小资”的标签,霞飞路的百乐门里紫醉金迷的生活恐怕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领略一番了。说句题外的,周老师傻就傻在觉得上海就是品味,就小资,以为这些气质从来都是上海气质的一部分。比如像旗袍这样的东西,其实说到底跟爵士乐一样都是外来的,只不过时间长了,旗袍就莫名其妙变成中国的“传统服饰”了。从老上海留下的纪录片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爵士乐正赶上摇摆乐(Swing)的时代,而爵士乐史上的第一个Legen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则扮演了传教士的角色,是他把摇摆爵士从芝加哥带到了纽约。纽约今天成为爵士乐的中心,他起了一定作用的。另外,老上海的爵士乐也仅限于歌舞厅,跟摇滚乐在八十年代刚到中国时的的遭遇相似,爵士乐也被国民政府当做是靡靡之音。
但相比较摇滚乐,爵士乐在中国难以发展的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爵士乐的传统和渊源很厚重。这种脱胎于布鲁斯的音乐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了,但布鲁斯又继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存在,继续影响着爵士乐和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摇滚乐。爵士乐刚传到老上海的时候,Ragtime的黄金时段已经结束了,但跟Ragtime一样,爵士乐也是作为给白人伴奏的舞曲出现的。但因为一战让美国大发了一笔战争财,爵士乐的诞生地新奥尔良有大量有才华的黑人乐手都跑到北方的大城市里赚钱了。跟早年杀到北京树村里的摇滚小青年们一样,这帮穷得丁零当啷响的黑哥们儿白天给各种饭店啊咖啡座啊刷盘子碗,晚上到舞厅里演奏爵士乐好让白人跳舞,于是芝加哥成了爵士乐新的中心。
但跟北京的摇滚小青年不一样的是,这帮黑哥们儿玩儿起乐器都是真功夫,哪里是只需要三和弦和荷尔蒙的朋克能比得了的,这是爵士乐在国内发展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摇滚自打娘胎里就是叛逆的产物,从嬉皮士运动和垮派作家的“嚎叫”中就能看出它的所有标签:离经叛道,蔑视传统,向往自由。这简直就是为文革后压抑中的青年们量身定做的,虽然摇滚乐一直被挤兑,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摇滚乐已经不完全属于地下亚文化了。开放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摇滚乐,走向大众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参演草莓和摩登天空音乐节的艺人名单来看,摇滚乐已经偏向流行,而只有流行才能商业化。在国外从来就没有真摇伪摇之争,因为摇滚乐在这里是大众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阻碍爵士乐传播的这第二个音乐在事实上使我们仅有的爵士音乐家们存活了下来。付不起房租又录不出唱片的树村青年们只能滚蛋回家,而刘元,刘玥这帮技术上牛逼闪闪的音乐家随便给人家上上课也能糊口了。
闲淡少扯,上图。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这是一号出场的第一支乐队Sara Marreiros,主唱的父亲是葡萄牙人,融合了南欧拉丁风的爵士乐是我的大爱。最左边是意大利乐器曼陀铃,那个小提琴手是现场认识的,也就是当天第二支乐队的小提琴手。即兴布吉乌吉(Boogie Woogie)的时代就成了爵士乐的一部分了。从最初的阿姆斯特朗到Bepop时代的查理帕克又到后来冷爵士时代的Miles Davis,Themonius Monk,哪个不是即兴大师。
这是二号下午第二支乐队Nick La Riviere,我第一次看到正式演出吹奏海螺,因为音准无法精确控制,这哥们儿用手放进放出来调整气柱的流畅度。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号作为领奏。早期的爵士乐是短号(后来很少用了,因为音域跟小号一样却不如小号富于变化就被取代了)领奏,长号只是在低音区用滑音跟短号做和弦上的呼应。钢琴因为搬运太困难,早期很少用。左二是弦贝斯(很多很多人说这是大提琴,不是的),与电贝司一样负责低音的演奏。早期由于录音设备没法对弦贝斯拾音,低音都是用大号来演奏。(也叫抱号,还记得七八年前张老师跟我讲,因为太大了要抱着吹,所以叫抱号,哈哈)最右边是两个小提琴,取代了原来铜管和木管乐器作为主角时代的的黑管儿。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三号的第三支乐队Soul Shaker,吉他手看起来范儿太正了。曲风偏向R&B(以为周杰伦是R&B的请掉头)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这是本届音乐节最后一支热辣火爆的高中生乐队,听介绍感觉像张帆搞得那种学校,人数很多,学生们轮番上阵。左一是低音萨克斯,左二左三是中音和次中音,被挡住的是小号,三个合音后面还有电吉他和电贝司,中间是爵士鼓。从一开始,大乐团就是爵士乐除了伴舞的舞曲之外的又一个特征。但电视发明之后这个玩意儿是如此新奇以至于人们不再热衷于晚上去舞厅了,一个标准的16人的大乐团要巡演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只好走向小型化。
在华语流行音乐界第一次出现合音到前台上伴舞的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高凌风带着他的御用合音“阿珠”和“阿花”激情演绎“冬天里的一把火”(没错,这不是费翔的歌),之后此举风靡台湾,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学国外的,知道了任贤齐刘若英等等台湾艺人全是扒日本的,王菲扒的是卡百利。在闭塞的年代里,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谁叫我们“与人斗其乐无穷”来着。
看看这些孩子吧,他们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里,女孩子们都水灵粉嫩的,有一个合音还戴着牙套呢,可爱死了。我们那么大的时候又在干嘛。中国的中小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像民工,因为具有流动的特点——你毕业了就不再属于高中生这个弱势群体了,于是他们的声音就一直无法发出来,无人关注。所以韩寒有多牛逼,我最知道。同时一并感谢我音乐上的带路人张老师,你一定知道,高中时那段有音乐陪伴的日子,对我的人生是多么多么重要。
PS听到现场版的What'd I Say真是个惊喜啊,真希望能听到Ray Charles亲自唱这首歌,呵呵。最后这支乐队分明就是谁牛逼就翻唱谁的,还有Etta James若干首, Stevie Wonder的“Higher Ground”,“Signed, Sealed, Delivered”, Billie Holliday, 等等等等一堆后悔没背歌词的好歌。
July 6.2010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躁动联合社周年纪念
去年的这个时间前后,我跟我的朋友于小杉在佳世客的一家音像店门口看到一张唐朝乐队演唱会的宣传海报,上面留有一个QQ群的联系方式方便订票,我就顺手记下来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清楚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将有怎样的影响。
作为一个一贯清高的人,我总是不屑于找到任何“组织”,单打独斗是我的个性。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在一个小城市里即使能找到一个一起听“枪炮与玫瑰”的朋友都是件挺困难的事情。同任何一个刚刚迷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所有文艺青年一样,我那时经常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幻觉中。随后我接触到了被我称为“中国的滚石杂志”的《我爱摇滚乐》,并且开始在RockBBS上通过写乐评结交朋友,但作为一个自认为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科班生,在面对当时众多只有理想没有技术的乐队时,我仍旧保持着一种优越感。虽然在现在看来,这种优越感正是来源于对现实的失望:除了跟师范学院音乐系的一个朋友交流音乐以外,我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可以交换CD听的人(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收藏打口碟数目最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对这个城市的音乐亚文化发展失去了兴趣。加之我看了一些关于中国摇滚乐现状的纪录片,我以为摇滚乐这玩意儿看来真是人家洋鬼子的东西,也许就没法在中国生根发芽吧。我关起门来,自己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现在看来,这种幼稚的判断跟所有处于悲观期的群体的想法是一个路数: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性解放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但实际上,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自动的“适合”任何一个国家,你能找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呢?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要宗教群体的国家,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其保守程度曾令人发指。摇滚乐这种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在美国的摇滚乐史中,猫王曾经因其歌曲的煽动性而造成当时青少年父母的巨大恐慌。在其他地区的摇滚乐史上,乐队也都是从地下状态慢慢发展到半地下,最终实现了成熟的商业化的。仅以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迷摇滚乐的时候全中国仅有迷笛音乐节这一个大型亚文化盛宴,但看看最近几年的状况吧:迷笛、摩登天空、成都热波、玉龙雪山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西湖音乐节……
诚然,近年这些音乐节也并不全由地下乐队的表演组成,乐迷的成分也开始复杂了起来。这时又有一帮傻X开始抱怨了:妈的这些都是“伪摇”。哎,你让人很难做啊,这东西不流行的时候你埋怨它不流行,现在流行了你又埋怨它流行了。我承认摇滚乐的力量来自她的真实,但从宏观的眼光来看,摇滚乐的发展从来都是跟女人(果儿)、商业、虚荣、乐队之间和乐队内部的争名夺利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猫王的走红就是商业宣传的结果:他们让一个白人去唱黑人的歌。所以在我看来,“伪摇”的增多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一种地下文化正在逐渐走向大众化。
就如同民主宪政的完成总要有一些人去实践一样,摇滚乐向大众化的转变同样需要有人推波助澜。在这个小城市里,摇滚乐的演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都需要有人去做。听听过去这一年在烟台演出的乐队的名字吧:崔健、唐朝、谢天笑、许巍、重塑雕像的权利、庙、玛雅、轩辕、大妈辣妈、张铁、逃跑计划、李志。除了前四个,都是一个叫做躁动联合社的团体争取的结果。青岛是胶东地区摇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躁动联合社不计任何报酬,从对联系演出一无所知开始,向青岛自由古巴的张大哥学习酒吧演出的商业模式,有乐队到青岛就争取他们到烟台作为下一站,就这样逐渐繁荣了这座小城市的文化市场。这个已经实现了半专业化的团队里的主要成员有美工鲍勃玛利(已婚)、二炮、灰尘、鲁子、吉洛的小马……(后面一百多个名字省略)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有一个:对理想的执着。正如鲍勃码利说的一样:“我们义务的做摇滚的广播员,而且我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经济方面的付出,但我们赢得了摇滚的繁荣和朋友们的友谊,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聚集在一起,在摇滚的天地里亲近着。乌托邦这个词,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义。我们可能没有能力组建乐队,没有可能资助摇滚是也,但就在这样的民间团体的努力下,这种文化会繁荣的。而且,她也真的繁荣了。”
非常荣幸曾经跟一群踏踏实实真真正正做事情的人共事过。躁动联合社,一周岁生日快乐。
作为一个一贯清高的人,我总是不屑于找到任何“组织”,单打独斗是我的个性。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在一个小城市里即使能找到一个一起听“枪炮与玫瑰”的朋友都是件挺困难的事情。同任何一个刚刚迷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所有文艺青年一样,我那时经常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幻觉中。随后我接触到了被我称为“中国的滚石杂志”的《我爱摇滚乐》,并且开始在RockBBS上通过写乐评结交朋友,但作为一个自认为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科班生,在面对当时众多只有理想没有技术的乐队时,我仍旧保持着一种优越感。虽然在现在看来,这种优越感正是来源于对现实的失望:除了跟师范学院音乐系的一个朋友交流音乐以外,我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可以交换CD听的人(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收藏打口碟数目最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对这个城市的音乐亚文化发展失去了兴趣。加之我看了一些关于中国摇滚乐现状的纪录片,我以为摇滚乐这玩意儿看来真是人家洋鬼子的东西,也许就没法在中国生根发芽吧。我关起门来,自己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现在看来,这种幼稚的判断跟所有处于悲观期的群体的想法是一个路数: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性解放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但实际上,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自动的“适合”任何一个国家,你能找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呢?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要宗教群体的国家,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其保守程度曾令人发指。摇滚乐这种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在美国的摇滚乐史中,猫王曾经因其歌曲的煽动性而造成当时青少年父母的巨大恐慌。在其他地区的摇滚乐史上,乐队也都是从地下状态慢慢发展到半地下,最终实现了成熟的商业化的。仅以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迷摇滚乐的时候全中国仅有迷笛音乐节这一个大型亚文化盛宴,但看看最近几年的状况吧:迷笛、摩登天空、成都热波、玉龙雪山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西湖音乐节……
诚然,近年这些音乐节也并不全由地下乐队的表演组成,乐迷的成分也开始复杂了起来。这时又有一帮傻X开始抱怨了:妈的这些都是“伪摇”。哎,你让人很难做啊,这东西不流行的时候你埋怨它不流行,现在流行了你又埋怨它流行了。我承认摇滚乐的力量来自她的真实,但从宏观的眼光来看,摇滚乐的发展从来都是跟女人(果儿)、商业、虚荣、乐队之间和乐队内部的争名夺利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猫王的走红就是商业宣传的结果:他们让一个白人去唱黑人的歌。所以在我看来,“伪摇”的增多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一种地下文化正在逐渐走向大众化。
就如同民主宪政的完成总要有一些人去实践一样,摇滚乐向大众化的转变同样需要有人推波助澜。在这个小城市里,摇滚乐的演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都需要有人去做。听听过去这一年在烟台演出的乐队的名字吧:崔健、唐朝、谢天笑、许巍、重塑雕像的权利、庙、玛雅、轩辕、大妈辣妈、张铁、逃跑计划、李志。除了前四个,都是一个叫做躁动联合社的团体争取的结果。青岛是胶东地区摇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躁动联合社不计任何报酬,从对联系演出一无所知开始,向青岛自由古巴的张大哥学习酒吧演出的商业模式,有乐队到青岛就争取他们到烟台作为下一站,就这样逐渐繁荣了这座小城市的文化市场。这个已经实现了半专业化的团队里的主要成员有美工鲍勃玛利(已婚)、二炮、灰尘、鲁子、吉洛的小马……(后面一百多个名字省略)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有一个:对理想的执着。正如鲍勃码利说的一样:“我们义务的做摇滚的广播员,而且我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经济方面的付出,但我们赢得了摇滚的繁荣和朋友们的友谊,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聚集在一起,在摇滚的天地里亲近着。乌托邦这个词,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义。我们可能没有能力组建乐队,没有可能资助摇滚是也,但就在这样的民间团体的努力下,这种文化会繁荣的。而且,她也真的繁荣了。”
非常荣幸曾经跟一群踏踏实实真真正正做事情的人共事过。躁动联合社,一周岁生日快乐。
2009年9月3日星期四
连我都看不懂的情色电影一定不是好电影
最近正抽空看各国的禁片,因为在印象中,国产的好片大都是禁片。但是顺着这个思路去找国外的禁片看会死得很惨。国内的好片子被广电总急毙掉的原因几乎都是因为涉及了所谓敏感题材(都他妈是中国人,我就不解释了),而国外的禁片大多是被认为违反了社会大众约定俗称的伦理道德标准,比如《洛丽塔》、《儿子与情人》,《地狱圣婴》,或挑战了人类的视听审美极限,如《一个人和他的猪》,以及我上午刚欣赏完的《我唾弃你的坟墓》。
我从这部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电影(导演毫不吝啬地给了强奸和屠戮镜头十多分钟)中完全体会不到导演想要传递什么东西。我甚至被影片刚开始时的文艺气息给骗到了,以至于看到中间部分还固执地认为影片最后一定会有出人意料的地方,直到愤怒地发现它被禁掉的理由如此简单——Disgusting.
所谓禁片只是不允许影院公开放映的电影,换句话说是不适合大众集体观看的,不代表禁止重口味的电影爱好者在家观摩,上头没这个权利。所以情色和暴力电影与普通的电影只是在于题材上有所不同,跟很多黄色笑话的路子是一致的——大多数情况下,性本身并不是重点。如以下笑话:
一对乌龟在沙滩上做爱,结束后两情相悦,决定来年相约同一时间在同一片海滩相见。第二年公海龟刚爬上沙滩就远远发现母海龟已等候在此,于是热泪盈眶地爬到母龟身旁,却只听母龟怒吼:他妈的!干完了老娘也不把老娘的壳儿顺手翻过来!让老娘在这儿白白躺了一年!
同理,导演最终还是想要通过这些非常规手段来表达他的观点,比如布雷娅在《地狱解剖》中的女性主义。但毕竟不是每个人在看到《地狱解剖》中男主角沾满女主角经血的勃起鸡8和女主角涂了口红的阴唇的时候能让自己的心理活动比生理活动更剧烈,于是它们就要理所当然地被禁掉了。
注:我一直认为情色电影是个很搞笑的词,只是那些制片人因为国内没有电影分级制度而生生憋出来的词,以示与色情电影不相为谋。并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有情节的就叫情色电影,没情节的就叫色情电影。要知道,A片也一样分为有情节的和没情节的。
文/醉海豚
07/04/09
我从这部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电影(导演毫不吝啬地给了强奸和屠戮镜头十多分钟)中完全体会不到导演想要传递什么东西。我甚至被影片刚开始时的文艺气息给骗到了,以至于看到中间部分还固执地认为影片最后一定会有出人意料的地方,直到愤怒地发现它被禁掉的理由如此简单——Disgusting.
所谓禁片只是不允许影院公开放映的电影,换句话说是不适合大众集体观看的,不代表禁止重口味的电影爱好者在家观摩,上头没这个权利。所以情色和暴力电影与普通的电影只是在于题材上有所不同,跟很多黄色笑话的路子是一致的——大多数情况下,性本身并不是重点。如以下笑话:
一对乌龟在沙滩上做爱,结束后两情相悦,决定来年相约同一时间在同一片海滩相见。第二年公海龟刚爬上沙滩就远远发现母海龟已等候在此,于是热泪盈眶地爬到母龟身旁,却只听母龟怒吼:他妈的!干完了老娘也不把老娘的壳儿顺手翻过来!让老娘在这儿白白躺了一年!
同理,导演最终还是想要通过这些非常规手段来表达他的观点,比如布雷娅在《地狱解剖》中的女性主义。但毕竟不是每个人在看到《地狱解剖》中男主角沾满女主角经血的勃起鸡8和女主角涂了口红的阴唇的时候能让自己的心理活动比生理活动更剧烈,于是它们就要理所当然地被禁掉了。
注:我一直认为情色电影是个很搞笑的词,只是那些制片人因为国内没有电影分级制度而生生憋出来的词,以示与色情电影不相为谋。并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有情节的就叫情色电影,没情节的就叫色情电影。要知道,A片也一样分为有情节的和没情节的。
文/醉海豚
07/04/09
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人人心中都住着厉鬼
“这部电影我等了很久了。”
“是啊,好像这部片子拍了两年多呢。”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像这样的一部电影,让我等了很久。现在你知道了,这并不是一部什么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了吧。”
看完陆川的第三部片子《南京!南京!》走出扬州淮海路影城,我这样跟同去的丹妮小朋友解释。
爱国主义这个词,虽然说是用“爱”字作为开头,却只会教给人们如何去仇恨。如果陆川的这部片子还是像那些传统的抗日题材电影一样,仅就仇恨而谈仇恨,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也更不可能触摸到一个真实的人性。其实从我十年前接触到石川达三写的《活着的士兵》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性是什么。
从孟子的性善论,到荀子的性恶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都在思考这个永恒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主张性善还是性恶都是不全面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都向往美好的事物,有良知,懂友爱;另一方面,我们又像基督教义主张的那样,生而背负着懒惰、贪婪、嫉妒等七宗罪来到这个人世间。它们共同构成了真实的人性。
我们从小孩子身上可以明显觉察到这种自相矛盾的真实:一个婴儿可以天真无邪,也可以邪恶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小孩子有时候可以善良地帮助老弱病残,富有同情心,但有时候也可以蛮不讲理地欺侮同伴;有时候我们对父母怀有强烈的淳朴的爱,但有时候又讨厌甚至怨恨他们。关于这种矛盾,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心理分析》里这样解释:
人类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包含了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性欲(libido,这是弗老大自己造的一个词,跟性欲sexual impulse还不一样)。“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它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现实,调节二者之间的冲突。“超我”则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知),与“本我”处于对立地位,它不仅使“本我”推迟得到满足,而且使之不能得到满足。是它在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在我看来,婴儿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自我”不断压抑“本我”的过程。
心理学是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但如果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战争下的人性,就是“自我”,“本我”,“超我”三者关系严重失衡时的状态。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环境中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使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婴儿的成长过程就是受到社会道德习俗影响的“自我”不断压抑“自我”的过程。但一旦这个或宏观或围观的社会环境处于非常态,比如战争下,暴行便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类之中,并非日本侵华日军所独有。如果电影不能揭示这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的非理性成分,那么一切对于战争的反思都是浅薄和无力的。甚至当我们是仅仅短暂脱离社会伦理监视下心理状态也会产生变化,我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捡到一个钱包和在一个僻静小巷里捡到一个钱包,心理也会不同,更何况是在1937的南京,那里没有道德,没有约束,没有伦理,更没有法律。
因此,影片结束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没有愤怒和仇恨,只有悲伤。侵华战争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耻辱,它是全人类的耻辱,是关于战争竟然可以将人性中如此丑陋的东西挖掘出来的耻辱。没有变态的日本人,只有变态的人。我相信这也是角川最后选择自杀的缘故,作为一个本来还有良知的人,当他发现这场战争把自己的人性摧残到自己都难以忍受的地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勇气背负着这样的重担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活下去,比死亡更艰难吧”。
除此之外,这部电影对国民党军官和叛徒的形象也选择了真实的反应而没有采取传统抗日题材中的丑化手段。大多数国民党军官都在诸如黄埔军校这样的名校里受过正规教育,因此更加儒雅。相比而言,红军军官才大多是一脸匪气。影片中刘烨扮演的小军官就作为一个正面角色进行了刻画。至于范伟扮演的叛徒,导演也将其内心的矛盾刻画出来了,尤其是在最后关头用自己死换取了别人的生。虽然影片没有交代,但我认为这个举动第一就是来源于为了自己的妻儿出卖了同胞的负罪感,第二个原因就体现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里,“你知道吗?我老婆又怀孕了。”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又得到了延续。
在大多数传统爱国主义电影让左粪们烧红了双眼声讨侵华日军的暴行的时候,这部电影让我再次看清了人性中的黑暗。这种黑暗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让人绝望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是可以警醒我们每一个人的。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基耶洛夫所说:黑色的主题同样蕴藏着“内在的净化和充满生命的力量”,“它包含着一种仁爱,这种仁爱在丑恶的东西中陷得越深,被人理解得也就越深,它包含着一种必须使痛苦达到终极的绝望,以便发现,同情是没有极限的。”人们能为普通的痛苦共鸣和呼吁,但是人们在真相面前,总要转过脸去。和大多数人一样,大多数电影在面对深切苦难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逃避或保持缄默。此时,只有用黑暗来告诉人们苦难的存在。因此,如果光明不能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就让黑暗来说话,至少黑暗不会给我们幻觉,让我们受到蒙蔽。而我们透过黑暗,却能看到更多的真实。
如果我将来会有孩子,我一定要教会她去尊重生命,告诉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是会哭会笑,有血有肉的生灵,这才是这部揭露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真实的黑暗的电影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文/munhokim
“是啊,好像这部片子拍了两年多呢。”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像这样的一部电影,让我等了很久。现在你知道了,这并不是一部什么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了吧。”
看完陆川的第三部片子《南京!南京!》走出扬州淮海路影城,我这样跟同去的丹妮小朋友解释。
爱国主义这个词,虽然说是用“爱”字作为开头,却只会教给人们如何去仇恨。如果陆川的这部片子还是像那些传统的抗日题材电影一样,仅就仇恨而谈仇恨,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也更不可能触摸到一个真实的人性。其实从我十年前接触到石川达三写的《活着的士兵》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性是什么。
从孟子的性善论,到荀子的性恶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都在思考这个永恒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主张性善还是性恶都是不全面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都向往美好的事物,有良知,懂友爱;另一方面,我们又像基督教义主张的那样,生而背负着懒惰、贪婪、嫉妒等七宗罪来到这个人世间。它们共同构成了真实的人性。
我们从小孩子身上可以明显觉察到这种自相矛盾的真实:一个婴儿可以天真无邪,也可以邪恶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小孩子有时候可以善良地帮助老弱病残,富有同情心,但有时候也可以蛮不讲理地欺侮同伴;有时候我们对父母怀有强烈的淳朴的爱,但有时候又讨厌甚至怨恨他们。关于这种矛盾,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心理分析》里这样解释:
人类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包含了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性欲(libido,这是弗老大自己造的一个词,跟性欲sexual impulse还不一样)。“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它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现实,调节二者之间的冲突。“超我”则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知),与“本我”处于对立地位,它不仅使“本我”推迟得到满足,而且使之不能得到满足。是它在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在我看来,婴儿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自我”不断压抑“本我”的过程。
心理学是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但如果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战争下的人性,就是“自我”,“本我”,“超我”三者关系严重失衡时的状态。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环境中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使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婴儿的成长过程就是受到社会道德习俗影响的“自我”不断压抑“自我”的过程。但一旦这个或宏观或围观的社会环境处于非常态,比如战争下,暴行便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类之中,并非日本侵华日军所独有。如果电影不能揭示这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的非理性成分,那么一切对于战争的反思都是浅薄和无力的。甚至当我们是仅仅短暂脱离社会伦理监视下心理状态也会产生变化,我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捡到一个钱包和在一个僻静小巷里捡到一个钱包,心理也会不同,更何况是在1937的南京,那里没有道德,没有约束,没有伦理,更没有法律。
因此,影片结束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没有愤怒和仇恨,只有悲伤。侵华战争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耻辱,它是全人类的耻辱,是关于战争竟然可以将人性中如此丑陋的东西挖掘出来的耻辱。没有变态的日本人,只有变态的人。我相信这也是角川最后选择自杀的缘故,作为一个本来还有良知的人,当他发现这场战争把自己的人性摧残到自己都难以忍受的地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勇气背负着这样的重担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活下去,比死亡更艰难吧”。
除此之外,这部电影对国民党军官和叛徒的形象也选择了真实的反应而没有采取传统抗日题材中的丑化手段。大多数国民党军官都在诸如黄埔军校这样的名校里受过正规教育,因此更加儒雅。相比而言,红军军官才大多是一脸匪气。影片中刘烨扮演的小军官就作为一个正面角色进行了刻画。至于范伟扮演的叛徒,导演也将其内心的矛盾刻画出来了,尤其是在最后关头用自己死换取了别人的生。虽然影片没有交代,但我认为这个举动第一就是来源于为了自己的妻儿出卖了同胞的负罪感,第二个原因就体现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里,“你知道吗?我老婆又怀孕了。”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又得到了延续。
在大多数传统爱国主义电影让左粪们烧红了双眼声讨侵华日军的暴行的时候,这部电影让我再次看清了人性中的黑暗。这种黑暗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让人绝望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是可以警醒我们每一个人的。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基耶洛夫所说:黑色的主题同样蕴藏着“内在的净化和充满生命的力量”,“它包含着一种仁爱,这种仁爱在丑恶的东西中陷得越深,被人理解得也就越深,它包含着一种必须使痛苦达到终极的绝望,以便发现,同情是没有极限的。”人们能为普通的痛苦共鸣和呼吁,但是人们在真相面前,总要转过脸去。和大多数人一样,大多数电影在面对深切苦难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逃避或保持缄默。此时,只有用黑暗来告诉人们苦难的存在。因此,如果光明不能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就让黑暗来说话,至少黑暗不会给我们幻觉,让我们受到蒙蔽。而我们透过黑暗,却能看到更多的真实。
如果我将来会有孩子,我一定要教会她去尊重生命,告诉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是会哭会笑,有血有肉的生灵,这才是这部揭露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真实的黑暗的电影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文/munhokim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爵士乐超简史
爵士乐的源头是在错综复杂不易考证,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由黑人民歌发展儿来,是由非洲的黑奴带到美洲去并扎下根来的。他们从各自的古老文化传统中撕裂开来,将民歌发展成为以歌曲讲故事的一种新的交流形式。美洲的黑人音乐保存了大量非洲特色,节奏特色明显,这种传统与移民地人民的音乐结合起来,结果诞生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声音而是一种全新的音乐表达形式。在蓄奴制被废除后,黑人音乐的发展很快。军乐团所弃用的乐器加上新获得的迁徙自由形成了爵士乐的根底:铜管乐,舞曲,布鲁斯。
布鲁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看似简单,实际可以有几乎是无穷的变化,一直是任何一种爵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成功地保持了自身独立的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布鲁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摇滚乐。简单说明一般布鲁斯的特点就是:它以每八或十二小节为一个乐段的音乐所组成,歌词紧密,它的“忧郁(蓝色)”特色产生的原因是将音阶中的E音及B音降了半音。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美国绝大多数南部城市内,都出现了黑人铜管乐队。与此同时,美国北部的黑人音乐倾向于欧陆风格。在该时期,Ragtime(拉格泰姆)开始形成。Ragtime的黄金时代大约是到二十世纪初,但它的影响绵延不绝。Ragtime与早期爵士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内,爵士乐逐渐形成,首先出现在美国南部城市黑人工人居住区内。和拉格泰姆一样,爵士乐最初也是作为舞曲出现的。最早成为早期爵士乐同义词的城市是新奥尔良,这种几近夸大的说法说明新奥尔良在爵士乐诞生及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比起其它地方可能是种类更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新奥尔良是产生爵士乐唯一的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有相当数量黑人聚居的美国南部城市所产生的音乐都应被视为是早期爵士乐的一种。其它城市还有亚特兰大,巴尔的摩。
许多人包括一些资深的爵士乐迷都相信早期的爵士音乐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天才,认为他们既不识谱又没上过一天音乐课。这种说法浪漫有余,可是谬之千里。几乎所有早期爵士乐中重要人物至少在正统音乐基础方面都是很扎实的,有些造诣还要更深。但是他们在乐器使用上的创新精神仍是独具的。最显著的例子要数Joseph O1iver,一个短号手。他曾使用过你能想象到的各种东西,饮水杯,装沙子的桶,浴缸塑料水塞之类的东西来使他的短号吹出多种音色变化。当时的典型爵士乐队的乐器包括短号或小号,长号,单簧管,吉他,低音提琴及鼓。钢琴因为不便搬运,所以很少使用。早期爵士现在给人的印象是班卓琴和大号比较突出,这是因为早期的录音技术还不能对声音更轻柔的吉他和低音提琴进行拾音。在当时担任领奏的是短号,长号作和弦呼应,最早作即兴演奏的是单簧管手。
到一战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工业因其得到了巨大发展,很多爵士乐手为了在北方工业城市里得到一份好工作纷纷向北迁移,Joseph O1iver也移居芝加哥。他原来在老家最好的一支乐队里,为填补他的空缺,他推荐了当时年仅18岁的Louis Armstrong(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个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人物。不仅对于爵士乐,还有摇摆乐。
对于富于创造力的天才Louis Armstrong来说,传统无疑就像一道紧箍咒。在二十年代年后期他接受了纽约最具声望的黑人乐队领袖Fletcher Henderson的邀请,他的风格特点就是在当时发展成熟起来的。在纽约的时候,Louis Armstrong也曾与后来被证明是最伟大的布鲁斯歌手的Bessie Smith合作录过唱片。后来Louis回到芝加哥,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和一个小乐队“热力五入组”(Hot Five)录制唱片。可以说电唱机的发明对当时爵士乐的传播乃至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的技艺日臻精进。路易斯在二十年代的乐坛上一时风头无二。甚至几乎一手促成了当时及以后的爵士音乐语汇的形成。
另外一位艺术生涯长达50多年的音乐家就是“公爵”Duke E11ington。E11ington的非凡才能不仅表现在音乐上,除了是一名出色的作曲家,编曲家,钢琴家,他还极具领导才能。许多著名的爵士乐好手都在E11ington的乐队里呆过,其中包括中低音萨克斯手Harry Carney,他的中音萨克斯成为爵士乐亮点之一;Joe Nanton,“会说话的”长号大师;小号手C1ark Terry等等。他本人对音乐的贡献也绝不仅限于爵士乐,一生写出了一千多首曲子,还有许多套曲,电影配乐,歌剧音乐,电视配乐,宗教音乐等等,可谓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
E11ington的兵器是钢琴。刚到纽约时,他的偶像是杰出的演奏家兼天才作曲家James P.Johnson。堪与James P.Johnson匹敌的是绰号为“雄狮”的Wi11ie Smith。这两人都是钢琴演奏中的“大踏(stride)”流派,特征为作为伴奏的左手演奏钢琴时特别用力。这些纽约的钢琴手们就促成了后来被称为“jam sessions”(即兴时期)的开始。而在芝加哥,一种风格殊异的钢琴风格在20年代后期出现。自从它的的典型代表Pinetop Smith写出了著名的代表作Boogie Woogie后,布吉伍吉就成为这种每节有八个低音波动的音乐风格的名称。
The Great Depression影响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爵士乐。唱片业到1931年已经跌落至谷底,但它依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但大萧条导致了伤感歌曲及浪漫低吟歌手开始大行其道。在摇摆乐的的盛世到来之前,那些后来的爵士新星几乎全部都在大乐团中演奏。这些人中有两位三十年代的爵士乐的先导者:人称“小爵士”(Little Jazz)的小号手Roy Eldridge,和人称“热度”(Chu)的Leon Berry。Roy是继Louis Armstrong之后影响力最大的小号手,风格热情奔放,音域辽阔,节奏强烈。
在“Swing”(摇摆乐)的时代里,Count Basie的乐团为全美爵士乐迷所熟悉,Count Basie给予了这支乐团独特的节奏特色,即平稳,典型的摇摆乐风格。摇摆乐时代不仅仅是大乐团时代或是小乐队独扬其声的时代。各种各样的音乐都被演奏过,包括以钢琴独奏的形式。
在以钢琴演奏爵士乐的音乐家中出类拔萃的要数Art Tatum。他在钢琴上的造诣给Vladimir Horowitz这样的古典音乐家都留下了印象。Tatum可能是所有爵士音乐家中技术上最有天分的一个。而且还不止仅此,他还有其它的过人之处,他的和弦感觉极为敏锐,这使得他的即兴演出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他的这种风格再加上他在节奏上的自由发挥而影响了一代年轻乐手,这些年轻乐手后来共同成为了又一种新的重要风格Bebop的奠基者。
二战敲响了大乐团的丧钟,一是巡回演出受到限制,二是部分很有才能的乐手被征召入伍,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大众趣味正在变化,摇摆舞音乐以不再受欢迎,人们开始转而喜欢浪漫情趣的歌谣。而那些捱过了战争年代的大乐团,很快就发现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竞争对象,那就是电视。越来越多的人们宁愿呆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出门,这导致了许多舞厅被迫关门大吉。如果继续按照大乐团的传统,即16个人辗转巡回演出,那费用就太高了。
但二战期间,我在上文提到的一种叫Bebop(比波普)的爵士乐诞生了,它的特点是和声复杂而动听,节奏繁复,向大众趣味也做了让步。领军人物是Charlie Parker,一位生长于堪萨斯市的中音萨克斯手。上学期Kasandera帮我从美国带回一张他的纪念版的唱片,在此一并感谢。
绰号“大鸟”的Charlie Parker是一个奇思泉涌的即兴演奏家,其想象力与他的技术互相辉映。其对爵士乐的影响我想只有Louis Armstrong可以相比。Charlie Parker早期的合作伙伴是小号手Dizzy Gilespie,他的技术几乎可与Charlie Parker媲美。当时另一个独步天下的音乐家是钢琴手兼作曲家Thelonius Monk,他音乐植根于“大踏”钢琴演奏传统。
Charlie Parker去世后,bop时代几乎终止,但是他的影响仍无处不在。这时冷爵士(Cool Jazz)开始出现,它的先锋是Miles Davis。我在五道口淘宝的时候曾经淘出一张他的绝世经典三套装。与Miles合作过的Sonny Rollins的即兴演奏在爵士乐中也极富想象力。同时代的John Coltrane虽然以小号手为人所熟知,但也吹奏次中音萨克斯及超高音萨克斯,他可能是Charlie Parker以后可以与Miles Davis并列影响最大的爵士乐手。后来这两人各自在自己选择的音乐道路上走得更远了。Miles的影响更多的启发了摇滚乐与爵士乐的融合,曾与Davis共事的著名乐手Herbie Hancock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开创了“Fusion”(融合爵士)的爵士风格。
这时,已经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扩展动摇了种族隔离的根基,但政府和白人对此或明或暗的抵制态度却比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期还要强烈了。这反而是黑人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求变得敏感而热切起来,个人主义化的自由爵士乐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出现的。自由爵士乐的出现被誉为爵士乐的“十月革命”,这是恰当的,它将爵士乐的即兴性发挥到了极点。也终于使爵士乐完成了从温情到愤怒,从含蓄到爆发,从抒情到放肆,从取悦式的表演到个体化表达的艺术坎途。
今天,爵士乐即使在美国的时髦青年眼中也不过是过气之物。在另一些人眼里也只是追求资产阶级奢靡情调的小市民的消费品。你也不要以为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混着Hip-Hop电子节奏的爵士乐还是爵士乐。爵士乐是黑人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自发的对本我个性根脉的抢救,绝大多数爵士乐是不需要演唱和歌词的,它在情感和美学上更接近音乐的原始模式。它不是像流行乐那样只去瘙痒你的肉体,而更多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寻到你灵魂深邃处的共鸣。
附录:如果你对爵士乐想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参照以下资料目录:
《爵士音乐史》(美)Tirro.F著
《爵士群像》(日)村上春树著(有中文译本)
《二十世纪的灵感——爵士乐》(中)程工著
《美国音乐家:56个爵士乐肖像》(美)Whitney.Blaaiett著
《Down Beat》美国最老字号的爵士乐杂志之一。电子版网址:www.downbeat.com
《Jazz Times》被誉为爵士乐界的《滚石》杂志
《哈姆区的伟大一天》介绍57个爵士乐巨匠的记录片
《女人一点里的诸个面孔》关于Billie Holiday传奇而悲剧的一生的电影
《在路上》Duke Ellington在欧洲巡演时的纪录片
《不停》Thelonious Monk最后一段弹琴的日子的记实,有很多精彩的现场片段。
布鲁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看似简单,实际可以有几乎是无穷的变化,一直是任何一种爵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成功地保持了自身独立的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布鲁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摇滚乐。简单说明一般布鲁斯的特点就是:它以每八或十二小节为一个乐段的音乐所组成,歌词紧密,它的“忧郁(蓝色)”特色产生的原因是将音阶中的E音及B音降了半音。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美国绝大多数南部城市内,都出现了黑人铜管乐队。与此同时,美国北部的黑人音乐倾向于欧陆风格。在该时期,Ragtime(拉格泰姆)开始形成。Ragtime的黄金时代大约是到二十世纪初,但它的影响绵延不绝。Ragtime与早期爵士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内,爵士乐逐渐形成,首先出现在美国南部城市黑人工人居住区内。和拉格泰姆一样,爵士乐最初也是作为舞曲出现的。最早成为早期爵士乐同义词的城市是新奥尔良,这种几近夸大的说法说明新奥尔良在爵士乐诞生及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比起其它地方可能是种类更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新奥尔良是产生爵士乐唯一的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有相当数量黑人聚居的美国南部城市所产生的音乐都应被视为是早期爵士乐的一种。其它城市还有亚特兰大,巴尔的摩。
许多人包括一些资深的爵士乐迷都相信早期的爵士音乐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天才,认为他们既不识谱又没上过一天音乐课。这种说法浪漫有余,可是谬之千里。几乎所有早期爵士乐中重要人物至少在正统音乐基础方面都是很扎实的,有些造诣还要更深。但是他们在乐器使用上的创新精神仍是独具的。最显著的例子要数Joseph O1iver,一个短号手。他曾使用过你能想象到的各种东西,饮水杯,装沙子的桶,浴缸塑料水塞之类的东西来使他的短号吹出多种音色变化。当时的典型爵士乐队的乐器包括短号或小号,长号,单簧管,吉他,低音提琴及鼓。钢琴因为不便搬运,所以很少使用。早期爵士现在给人的印象是班卓琴和大号比较突出,这是因为早期的录音技术还不能对声音更轻柔的吉他和低音提琴进行拾音。在当时担任领奏的是短号,长号作和弦呼应,最早作即兴演奏的是单簧管手。
到一战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工业因其得到了巨大发展,很多爵士乐手为了在北方工业城市里得到一份好工作纷纷向北迁移,Joseph O1iver也移居芝加哥。他原来在老家最好的一支乐队里,为填补他的空缺,他推荐了当时年仅18岁的Louis Armstrong(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个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人物。不仅对于爵士乐,还有摇摆乐。
对于富于创造力的天才Louis Armstrong来说,传统无疑就像一道紧箍咒。在二十年代年后期他接受了纽约最具声望的黑人乐队领袖Fletcher Henderson的邀请,他的风格特点就是在当时发展成熟起来的。在纽约的时候,Louis Armstrong也曾与后来被证明是最伟大的布鲁斯歌手的Bessie Smith合作录过唱片。后来Louis回到芝加哥,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和一个小乐队“热力五入组”(Hot Five)录制唱片。可以说电唱机的发明对当时爵士乐的传播乃至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的技艺日臻精进。路易斯在二十年代的乐坛上一时风头无二。甚至几乎一手促成了当时及以后的爵士音乐语汇的形成。
另外一位艺术生涯长达50多年的音乐家就是“公爵”Duke E11ington。E11ington的非凡才能不仅表现在音乐上,除了是一名出色的作曲家,编曲家,钢琴家,他还极具领导才能。许多著名的爵士乐好手都在E11ington的乐队里呆过,其中包括中低音萨克斯手Harry Carney,他的中音萨克斯成为爵士乐亮点之一;Joe Nanton,“会说话的”长号大师;小号手C1ark Terry等等。他本人对音乐的贡献也绝不仅限于爵士乐,一生写出了一千多首曲子,还有许多套曲,电影配乐,歌剧音乐,电视配乐,宗教音乐等等,可谓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
E11ington的兵器是钢琴。刚到纽约时,他的偶像是杰出的演奏家兼天才作曲家James P.Johnson。堪与James P.Johnson匹敌的是绰号为“雄狮”的Wi11ie Smith。这两人都是钢琴演奏中的“大踏(stride)”流派,特征为作为伴奏的左手演奏钢琴时特别用力。这些纽约的钢琴手们就促成了后来被称为“jam sessions”(即兴时期)的开始。而在芝加哥,一种风格殊异的钢琴风格在20年代后期出现。自从它的的典型代表Pinetop Smith写出了著名的代表作Boogie Woogie后,布吉伍吉就成为这种每节有八个低音波动的音乐风格的名称。
The Great Depression影响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爵士乐。唱片业到1931年已经跌落至谷底,但它依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但大萧条导致了伤感歌曲及浪漫低吟歌手开始大行其道。在摇摆乐的的盛世到来之前,那些后来的爵士新星几乎全部都在大乐团中演奏。这些人中有两位三十年代的爵士乐的先导者:人称“小爵士”(Little Jazz)的小号手Roy Eldridge,和人称“热度”(Chu)的Leon Berry。Roy是继Louis Armstrong之后影响力最大的小号手,风格热情奔放,音域辽阔,节奏强烈。
在“Swing”(摇摆乐)的时代里,Count Basie的乐团为全美爵士乐迷所熟悉,Count Basie给予了这支乐团独特的节奏特色,即平稳,典型的摇摆乐风格。摇摆乐时代不仅仅是大乐团时代或是小乐队独扬其声的时代。各种各样的音乐都被演奏过,包括以钢琴独奏的形式。
在以钢琴演奏爵士乐的音乐家中出类拔萃的要数Art Tatum。他在钢琴上的造诣给Vladimir Horowitz这样的古典音乐家都留下了印象。Tatum可能是所有爵士音乐家中技术上最有天分的一个。而且还不止仅此,他还有其它的过人之处,他的和弦感觉极为敏锐,这使得他的即兴演出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他的这种风格再加上他在节奏上的自由发挥而影响了一代年轻乐手,这些年轻乐手后来共同成为了又一种新的重要风格Bebop的奠基者。
二战敲响了大乐团的丧钟,一是巡回演出受到限制,二是部分很有才能的乐手被征召入伍,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大众趣味正在变化,摇摆舞音乐以不再受欢迎,人们开始转而喜欢浪漫情趣的歌谣。而那些捱过了战争年代的大乐团,很快就发现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竞争对象,那就是电视。越来越多的人们宁愿呆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出门,这导致了许多舞厅被迫关门大吉。如果继续按照大乐团的传统,即16个人辗转巡回演出,那费用就太高了。
但二战期间,我在上文提到的一种叫Bebop(比波普)的爵士乐诞生了,它的特点是和声复杂而动听,节奏繁复,向大众趣味也做了让步。领军人物是Charlie Parker,一位生长于堪萨斯市的中音萨克斯手。上学期Kasandera帮我从美国带回一张他的纪念版的唱片,在此一并感谢。
绰号“大鸟”的Charlie Parker是一个奇思泉涌的即兴演奏家,其想象力与他的技术互相辉映。其对爵士乐的影响我想只有Louis Armstrong可以相比。Charlie Parker早期的合作伙伴是小号手Dizzy Gilespie,他的技术几乎可与Charlie Parker媲美。当时另一个独步天下的音乐家是钢琴手兼作曲家Thelonius Monk,他音乐植根于“大踏”钢琴演奏传统。
Charlie Parker去世后,bop时代几乎终止,但是他的影响仍无处不在。这时冷爵士(Cool Jazz)开始出现,它的先锋是Miles Davis。我在五道口淘宝的时候曾经淘出一张他的绝世经典三套装。与Miles合作过的Sonny Rollins的即兴演奏在爵士乐中也极富想象力。同时代的John Coltrane虽然以小号手为人所熟知,但也吹奏次中音萨克斯及超高音萨克斯,他可能是Charlie Parker以后可以与Miles Davis并列影响最大的爵士乐手。后来这两人各自在自己选择的音乐道路上走得更远了。Miles的影响更多的启发了摇滚乐与爵士乐的融合,曾与Davis共事的著名乐手Herbie Hancock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开创了“Fusion”(融合爵士)的爵士风格。
这时,已经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扩展动摇了种族隔离的根基,但政府和白人对此或明或暗的抵制态度却比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期还要强烈了。这反而是黑人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求变得敏感而热切起来,个人主义化的自由爵士乐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出现的。自由爵士乐的出现被誉为爵士乐的“十月革命”,这是恰当的,它将爵士乐的即兴性发挥到了极点。也终于使爵士乐完成了从温情到愤怒,从含蓄到爆发,从抒情到放肆,从取悦式的表演到个体化表达的艺术坎途。
今天,爵士乐即使在美国的时髦青年眼中也不过是过气之物。在另一些人眼里也只是追求资产阶级奢靡情调的小市民的消费品。你也不要以为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混着Hip-Hop电子节奏的爵士乐还是爵士乐。爵士乐是黑人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自发的对本我个性根脉的抢救,绝大多数爵士乐是不需要演唱和歌词的,它在情感和美学上更接近音乐的原始模式。它不是像流行乐那样只去瘙痒你的肉体,而更多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寻到你灵魂深邃处的共鸣。
附录:如果你对爵士乐想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参照以下资料目录:
《爵士音乐史》(美)Tirro.F著
《爵士群像》(日)村上春树著(有中文译本)
《二十世纪的灵感——爵士乐》(中)程工著
《美国音乐家:56个爵士乐肖像》(美)Whitney.Blaaiett著
《Down Beat》美国最老字号的爵士乐杂志之一。电子版网址:www.downbeat.com
《Jazz Times》被誉为爵士乐界的《滚石》杂志
《哈姆区的伟大一天》介绍57个爵士乐巨匠的记录片
《女人一点里的诸个面孔》关于Billie Holiday传奇而悲剧的一生的电影
《在路上》Duke Ellington在欧洲巡演时的纪录片
《不停》Thelonious Monk最后一段弹琴的日子的记实,有很多精彩的现场片段。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