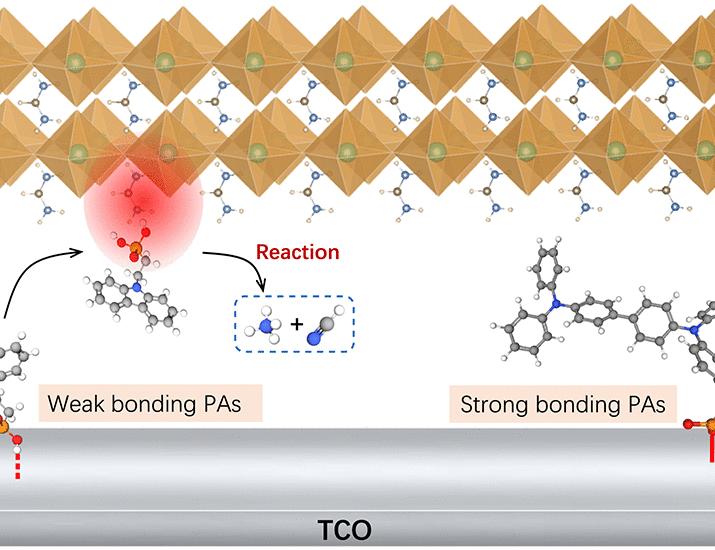历史系的Dr. Eric Sager今天下午准备了一个题为“The History of Long-Form Census in Canada”的小讲座,我想到这个月一号正好是中国的第六次全国普查启动日,作为一个关心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准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本着借鉴下外国经验教 训的目的去了一趟。
去之前简单google了一下了解背景知识。原来今年6月的时候加拿大联 邦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为由取消了自从1871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就延续至今的Mandatory Long Form。从2011年的普查开始采原有的Long Form将被一个自愿填写的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取代,原本就是自愿形式的Short Form将继续沿用(1871年至1951年均为10年一次,之后改为5年一次,即每逢年数尾号1或6则进行全国普查)。这个未经事先国会讨论的决议遭到 了来自全体公民一致的强烈反弹,无论是elite还是populist。因为人口普查采取自愿形式就无法保证普查数据的有效性。事实上,近年来加拿大普查 的response rates已经逐次下跌了,有接近美国的趋势(他们好像连总统选举都懒得去投票了)。在加拿大统计局的网站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公告:
“We have never previously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scale of the voluntary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nor are we aware of any other country that has. The new method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relatively rapidly with limited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mitigation strategies to offset non-response bias and other quality limiting effects is largely unknown. For these reasons, it is difficult to anticipate the quality level of the final outcome.”
http://www.statcan.gc.ca/survey-enquete/household-menages/nhs-enm-eng.htm
对 于像Sager这样在过去二十年里都要依靠统计局的数字作研究的学者来说,这种政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一个国家的任何公共政策都需要根据相应的人口资源状 况来制定,比如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移民政策的出台、刺激就业等。讲座的前半部分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制定的重大国家决策,如南北战争期 间xxx,城市化期间xxx,大萧条期间xxx(悲催的,我这次是下定决心买录音笔了!)另外还捎带讲了人口普查的四大原则和long form census是如何从十几个问题演变到涵盖了宗教、种族、职业、教育程度、病史、就业、母语、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背景等问题的调查问卷的。历史上当然也 出现过反对人口普查的声音,其理由正是因为人口资源的数据是如此重要,应当作为国家机密。比如1753年英国国会就以此为理由否决了进行人口普查的提案。 但是在现代国家中,只有盛产愚民的国家才会禁止公民(foreign or domestic)取得关于自己国家的人口数据。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取得中国的经济数据和失业率信息要比取得欧美国家的数据要难不知道多少倍。
来自平民的反弹也不难理解,在偏向于比较左的Social Democracy的福利国家,穷人更乐于接受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讲 座的后半部分Sager主要是在论证公民的隐私权其实是个明显的借口,因为在过去的20年的四次全国普查中,政府只收到了50封抱怨隐私权受到侵犯的来 信。而这种抱怨必然将普查视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了。在Sager看来,这是对普查的严重误读。因为这项举措除了让政策的制定者更好的了解其国民状况以 外,也创造了公民与国家对话的条件(这就是福柯所谓的权力永远是双向传递的意思吧),除此之外使公民之间的对话也成为可能。那么取消强制型问卷的动机到底 是什么呢?老头子没下结论,但他暗示了人口普查也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比如城市化期间,有一些问题被加入到了long form census是为了调查某些利益集团感兴趣的问题(悲催的,又没听完整)。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 悖论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却经常显示了在普查上贯彻力、统计技能、人力组织、动员能力的低下。这就是我以前提到过的三大悖论之一的最好注释,但凡具有 举国上下的贯彻执行力的国家都不会利用这种权力去做一件好事,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套户口制度,如果这套制度是如此有效,那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人口普 查,但这套制度仅仅会在限制人口流动这样的问题上显示出它的高效。
另一个因人口普查想到的问 题是它与民族国家的确立之间的关系。 ethnicity取代race成为社会科学中界定不同集团的概念仅仅是二战以后的事情,而人口普查也是相当晚近的产物,我隐约觉得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是“高山族”这一名称在大陆的确立,跟“印第安人”一词的确立很相似;汉族之间的差异其实也很大,一个广东人也许是马来人的后裔,一个 山东人的祖先可能是蒙古人种,但他们在国家权力的介入的下逐渐习惯汉族认同,并逐渐固定化。吴老师说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
PS1.如果有媒体约稿我再写篇深度报道吧,最近懒死了,什么都不想干。
PS2.丹我需要你,其他记者朋友还有推荐录音笔的吗?是啊是啊,我雅思听力8.5/9,托福也接近满分,毕业后还教过雅思,来了北美一年多,可还是没法在学术会把信息听全了。所以说什么把一个人扔国外就能学会外语,或者让他一个人生活就会学会做饭之类的,都是鬼话!
2010年11月23日星期二
2010年11月14日星期日
“为什么中国学生不是engineer就是scientist?”
北美老百姓心目中关于中国人的Stereotype,估计这个是最最普遍的一个了。不仅是华裔,在美国的中小学里, 亚裔普遍被认为是“模范族裔”。这些来自亚州移民家庭的孩子通常在学校中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和科学成绩经常出类拔萃;至于留学生群体情况有所不同,各个大学里的计算机和工程系的实验室里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的穷哥们儿们,很多实验室里根本就不用讲英文,连导师带学生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告诉别人自己就读于人文学院时,他们的反应经常是:WOW,我还以为中国留学生都是科学家呢!
其他亚非拉哥们儿的情况我不了解,我跟他们解释的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的情况了。
近代以前中国是没有文理科的概念的。学科的分类方法历朝历代都不一样,皇帝们经常下令文官们修书,汉朝的刘向奉帝整理皇家图书,他儿子根据他的目录学专著整理出了一种七分法叫“七略”:辑略,六艺略(就是六经,诗,书,礼,易之类),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计略。其中的辑略只不过是个总目,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个门类。后来又出现了更著名的四分法:经,史,子,集。纪昀整理的《四库全书》就是以此编辑。经部包括儒家经典以及研究这些经典诸如注释它们的书;史部是所有历史书和研究评价这些历史书的书;子部是兵,法,农,医,天文,算术等各家著作;集部是文学作品,如诗,词,赋,曲,散文。但无论怎么分,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都把儒学奉为经典,自从汉代儒家的地位被确定下来并不断强化,知识分子阶层同权力机构的联姻也不断强化,到隋唐科举制度确立,本来儒学局限在上流社会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社会,谁要取士都要学儒家经典,这注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会在中国出现,即便零星有理科的著作出现,也被认为是巫术,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
到了近代中国被迫跟世界有了联系,也就是在这时出现了文理科的概念,外来的科学技术都被归于理科,中国原有的儒学就是文科了。在经历了N次战争惨败后,代表中国“文科”的儒学就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根源所在,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这种分类法到了民国时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并不能都归于原有的理科范畴里,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于是这些学科被归到了文科一类。在这个转型时期里“文科”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了。《孔乙己》里代表的只是典型中国旧式文人形象,但现实中的“文人”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普遍被人们看做是“文人”的海归比如蔡元培,马寅初,胡适等,除了学到了西方的社科外,旧学功底也很深厚。这个时期的“文人” 社会地位非常高,收入也可观。
四九年是个分界线,清末以来试图以“理科”富国强兵的意识形态在毛时代达到了最高潮,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很多“文科”都调整没了,反应在民间的话语也就是所谓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例外情况是文革,那时无论文理都不受重视,那种反智的时代才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文革是中国出现第一波“读书无用论”的背景。改革开放之后虽然80年代经历了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但是理工科仍然为政治青睐。邓时代无论是“四个现代化”,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体现了这一点。其他的学科比如法学的现代化通常学者们认为以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为界,而别的学科如政治学和经济学出现现代性的年代自然会更晚。这段时间里“文人”的地位小有起伏,但总体情况是不理想,但“科学家” 们的地位就有明显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跟古代一样,知识的地位依然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目前的国家领导人,大部分是搞工程啊水力啊什么的。至此就可以部分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由于国家重视建设理工科,那么理工科的学生无论是就业还是留学都有相对好的出路。至于我们,只会给天朝捣乱,没出路也是活该。
但更纠结的问题是,“文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问题到现在还是一锅糊涂粥,而且我预感只要文理二元没有消除,就会永远糊涂下去,就像根据有没有鸡巴把人分成两类就造成了同性恋和易性癖的identity crisis一样。社科被搅到“文科”这趟浑水里,社科的发展就受限。首先老百姓不知道社科到底是干嘛的,因为老百姓觉得,“文科”嘛,除了唧唧歪歪还能干什么?换句话说,不务实。这是受中国旧式文人形象的影响,国外是没有的。并且,国外的知识分子跟弱不禁风的形象也没什么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除了要思考,还得养活自己,劈柴烧水样样都得自己来,不像中国古代的文人“万般皆下品”,只要当上了官,书里自有黄金美女。虽然对“文科”不持有贬低的态度,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也是用来提高个人修养的,更多针对个人而言,而社科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高中的文理班这个概念里,“文”指的更多的是人文,各个高中基本上都是理科学不动了的女生转到了文科班,但这些学生到了大学可能会去学经济学甚至法学。这些学科总不能也“勤能补拙”吧?反观其他国家,这些学科则拥有最优秀的生源,理工科学生反被老百姓认为是各种Geek。
综上,粗暴的二分法把“文科”搅浑了;传统文人形象根深蒂固;执政党刻意压制不利于其统治的学科,这些是中国重“理”轻“文”导致的学科建设落后的大致原因。
其他亚非拉哥们儿的情况我不了解,我跟他们解释的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的情况了。
近代以前中国是没有文理科的概念的。学科的分类方法历朝历代都不一样,皇帝们经常下令文官们修书,汉朝的刘向奉帝整理皇家图书,他儿子根据他的目录学专著整理出了一种七分法叫“七略”:辑略,六艺略(就是六经,诗,书,礼,易之类),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计略。其中的辑略只不过是个总目,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个门类。后来又出现了更著名的四分法:经,史,子,集。纪昀整理的《四库全书》就是以此编辑。经部包括儒家经典以及研究这些经典诸如注释它们的书;史部是所有历史书和研究评价这些历史书的书;子部是兵,法,农,医,天文,算术等各家著作;集部是文学作品,如诗,词,赋,曲,散文。但无论怎么分,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都把儒学奉为经典,自从汉代儒家的地位被确定下来并不断强化,知识分子阶层同权力机构的联姻也不断强化,到隋唐科举制度确立,本来儒学局限在上流社会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社会,谁要取士都要学儒家经典,这注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会在中国出现,即便零星有理科的著作出现,也被认为是巫术,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
到了近代中国被迫跟世界有了联系,也就是在这时出现了文理科的概念,外来的科学技术都被归于理科,中国原有的儒学就是文科了。在经历了N次战争惨败后,代表中国“文科”的儒学就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根源所在,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这种分类法到了民国时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并不能都归于原有的理科范畴里,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于是这些学科被归到了文科一类。在这个转型时期里“文科”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了。《孔乙己》里代表的只是典型中国旧式文人形象,但现实中的“文人”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普遍被人们看做是“文人”的海归比如蔡元培,马寅初,胡适等,除了学到了西方的社科外,旧学功底也很深厚。这个时期的“文人” 社会地位非常高,收入也可观。
四九年是个分界线,清末以来试图以“理科”富国强兵的意识形态在毛时代达到了最高潮,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很多“文科”都调整没了,反应在民间的话语也就是所谓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例外情况是文革,那时无论文理都不受重视,那种反智的时代才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文革是中国出现第一波“读书无用论”的背景。改革开放之后虽然80年代经历了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但是理工科仍然为政治青睐。邓时代无论是“四个现代化”,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体现了这一点。其他的学科比如法学的现代化通常学者们认为以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为界,而别的学科如政治学和经济学出现现代性的年代自然会更晚。这段时间里“文人”的地位小有起伏,但总体情况是不理想,但“科学家” 们的地位就有明显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跟古代一样,知识的地位依然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目前的国家领导人,大部分是搞工程啊水力啊什么的。至此就可以部分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由于国家重视建设理工科,那么理工科的学生无论是就业还是留学都有相对好的出路。至于我们,只会给天朝捣乱,没出路也是活该。
但更纠结的问题是,“文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问题到现在还是一锅糊涂粥,而且我预感只要文理二元没有消除,就会永远糊涂下去,就像根据有没有鸡巴把人分成两类就造成了同性恋和易性癖的identity crisis一样。社科被搅到“文科”这趟浑水里,社科的发展就受限。首先老百姓不知道社科到底是干嘛的,因为老百姓觉得,“文科”嘛,除了唧唧歪歪还能干什么?换句话说,不务实。这是受中国旧式文人形象的影响,国外是没有的。并且,国外的知识分子跟弱不禁风的形象也没什么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除了要思考,还得养活自己,劈柴烧水样样都得自己来,不像中国古代的文人“万般皆下品”,只要当上了官,书里自有黄金美女。虽然对“文科”不持有贬低的态度,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也是用来提高个人修养的,更多针对个人而言,而社科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高中的文理班这个概念里,“文”指的更多的是人文,各个高中基本上都是理科学不动了的女生转到了文科班,但这些学生到了大学可能会去学经济学甚至法学。这些学科总不能也“勤能补拙”吧?反观其他国家,这些学科则拥有最优秀的生源,理工科学生反被老百姓认为是各种Geek。
综上,粗暴的二分法把“文科”搅浑了;传统文人形象根深蒂固;执政党刻意压制不利于其统治的学科,这些是中国重“理”轻“文”导致的学科建设落后的大致原因。
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
刚从Ozzy Osbourne的现场尿裤子回来了
2个月前得知Ozzy要来这个城市演出的消息时我很吃惊,虽然我在下城也看到过零星的几家摇滚文化店,总觉得这个地方的重金属乐迷不会太多。再说了,该有多老才能当上Ozzy的乐迷呢?这个老家伙的唱片公司甚至隔上个几年把黑色安息日的老曲子编排一下出个精选集,或者找新的乐手给Ozzy配乐混编一下就能随便卖出几百张专辑了。今晚距上一次Ozzy携黑色安息日原班人马来维多利亚已经将近30年了,我没想到现场会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这也间接说明自由开放社会下的文化会更加多元吧?我开始听重金属的时候,朋克刚刚终结了一个“快乐得没心没肺”的金属时代,摇滚界发出“金属已死”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摇滚乐就跟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思潮一样,完全没有隔代这一说,现代后现代思潮是同时进入中国,我们也是摇滚后摇一起听大的(所以我老板听说我也喜欢The Who的时候很奇怪)。
年过六旬的老Ozzy唱了将近2个小时,另一个能连续又蹦又唱这么长时间的老家伙我目前只能想到Iggy Pop。但返场之前的最后一首歌Crazy Train的时候老家伙唱到高音一下子唱劈叉了,赶忙把话筒伸向了观众,反正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虽然掩过去了,但我在那一刻突然为这个当年的“黑暗王子”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难过。其实整场演出感动我的镜头还是不少的嘛,比如那些虔诚的小伙子们,我想他们的心情就跟我当年第一次听崔健现场时差不多吧;再比如唱“Dreamer”时满场的打火机。我还终于明白了混rockbbs的时候我们版的版主喜欢形容“军鼓声打得像炮弹一样”的感觉了。还有,这个老家伙保持了朝观众泼水的传统,但比起水桶,他显然更喜欢直接用高压水喉了……而且,而且水好像还是带白色颜料的。没借相机过去真是失策了。
我会唱的几首基本上全唱了,“Paranoid”, “Shot in the Dark”, “No More Tears”, “Crazy Train”, “Mr. Crowley”, 而且返场的时候竟然唱的是我最喜欢的这首Mama, I'm Coming Home,没唱“Goodbye to Romance”有点遗憾,但运气已经好得不像话了。当唱到“我已千万次注视过你的面庞,当我们彼此分离,我不在乎阳光雨露”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我扭过头就能吻到你的脸。
年过六旬的老Ozzy唱了将近2个小时,另一个能连续又蹦又唱这么长时间的老家伙我目前只能想到Iggy Pop。但返场之前的最后一首歌Crazy Train的时候老家伙唱到高音一下子唱劈叉了,赶忙把话筒伸向了观众,反正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虽然掩过去了,但我在那一刻突然为这个当年的“黑暗王子”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难过。其实整场演出感动我的镜头还是不少的嘛,比如那些虔诚的小伙子们,我想他们的心情就跟我当年第一次听崔健现场时差不多吧;再比如唱“Dreamer”时满场的打火机。我还终于明白了混rockbbs的时候我们版的版主喜欢形容“军鼓声打得像炮弹一样”的感觉了。还有,这个老家伙保持了朝观众泼水的传统,但比起水桶,他显然更喜欢直接用高压水喉了……而且,而且水好像还是带白色颜料的。没借相机过去真是失策了。
我会唱的几首基本上全唱了,“Paranoid”, “Shot in the Dark”, “No More Tears”, “Crazy Train”, “Mr. Crowley”, 而且返场的时候竟然唱的是我最喜欢的这首Mama, I'm Coming Home,没唱“Goodbye to Romance”有点遗憾,但运气已经好得不像话了。当唱到“我已千万次注视过你的面庞,当我们彼此分离,我不在乎阳光雨露”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我扭过头就能吻到你的脸。
2010年11月6日星期六
可我还是很失望
我刚从戴晴的演讲现现场回来,脑子比较乱,但我不觉得这种演讲值得我再多拿出几个小时整理一下素材组织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想到哪儿就扯到哪儿吧。虽然我去之前就猜戴晴其实也说不出什么一二三来,但冲着她的题目“Water Crisis in Beijing”,觉得总能扩充一些关于北京具体问题方面的一手材料吧。戴晴这次来计划做的一系列演讲根据Poster都应该是跟环境问题相关的,title写的也是Chinese environmentalist and journalist Dai Qing,这个场次应该讲水危机,下周一则应该讲三峡大坝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结果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水危机的情况,如果不算她展示了几张自然水体被严重污染的powerpoint的话。我几乎是强忍着才听完了她的控诉控诉控诉,绝大部分愤青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的话里只有态度态度态度,只有让人能够在情绪上有波动而无法引起我任何深刻思考的东西。“萨科奇跟胡锦涛刚刚签了一笔大合同暗示了他在诺奖上的态度,如果其他国家效仿,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灾难。”除了这个观点稍显新颖剩下的我甚至懒得打出全文,秦始皇啦,毛泽东恐吓郭沫若啦,习近平的近期表现啦,高GDP掩盖的环境问题啦,独裁啦,人权啦……
我还以为今天来听演讲的人总该都知道些关于中国的基本背景呢。
是的,这不是学术研讨会,戴晴也不是scholar,而是activist,跟我们的社会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总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吧。水危机?地上水还是地下水?过度开发导致的还是工业污染导致的?中国城市水资源概况是怎样的?只字未提。就连我在Q&A时间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她的正面回答。
“我想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在这些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事件中,您有没有看到一个与政府沟通协商的契机或者新的模式。因为在以往的环境问题中,比如三峡或者癌症村,我没有看到受影响的居民与政府产生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但我发现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垃圾问题和垃圾焚烧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走上街头,政府被迫作出反应。这让我想起台湾八十年代的垃圾战对解除戒严的积极作用了,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您觉得中国的垃圾战会不会成为一个产生新的市民与政府沟通的模式?”
结果她就敷衍过去了。于是我走出教室相比较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多知道任何事。虽然我从来都把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社会角色分得很清楚,甚至还很反感一些从来不参与改造现实的知识分子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刻薄态度,因为这些人批评这些社会活动家的观点,而我认为这不重要。刘也好,戴晴也好,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行为,而不是观点。再说整场演讲的气氛也挺欢乐的,Richard还主动上去帮忙口译,可爱死了,我真的爱死我老板了。
那我到底还在生哪门子气呢?
我还以为今天来听演讲的人总该都知道些关于中国的基本背景呢。
是的,这不是学术研讨会,戴晴也不是scholar,而是activist,跟我们的社会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总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吧。水危机?地上水还是地下水?过度开发导致的还是工业污染导致的?中国城市水资源概况是怎样的?只字未提。就连我在Q&A时间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她的正面回答。
“我想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在这些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事件中,您有没有看到一个与政府沟通协商的契机或者新的模式。因为在以往的环境问题中,比如三峡或者癌症村,我没有看到受影响的居民与政府产生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但我发现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垃圾问题和垃圾焚烧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走上街头,政府被迫作出反应。这让我想起台湾八十年代的垃圾战对解除戒严的积极作用了,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您觉得中国的垃圾战会不会成为一个产生新的市民与政府沟通的模式?”
结果她就敷衍过去了。于是我走出教室相比较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多知道任何事。虽然我从来都把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社会角色分得很清楚,甚至还很反感一些从来不参与改造现实的知识分子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刻薄态度,因为这些人批评这些社会活动家的观点,而我认为这不重要。刘也好,戴晴也好,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行为,而不是观点。再说整场演讲的气氛也挺欢乐的,Richard还主动上去帮忙口译,可爱死了,我真的爱死我老板了。
那我到底还在生哪门子气呢?
2010年11月1日星期一
三个悖论
每学期初校园里都会出现各种社会组织来纳新,我偶然看到过“第四国际”的摊位,第四国际是个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托派分子,比如李大钊、陈独秀),我没想到他们现在还在活跃着,于是上前与之攀谈。一个姑娘对我说:“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之所有没有成功,是因为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卡斯特罗等人都没有致力于形成国际工人组织,于是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孤立……看看资本主义是多么chaos,人们没有一致的目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这些行为都是由经济利益驱使的(英文大意如此)。我微笑地说,“That's the beauty of it.” 于是则有,
悖论一:在改变任何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感慨个人的渺小,希望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可凡是能够调动整个国家机器去高效率地完成一件事的政府,都不会做什么好事,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由悖论一倒推出悖论二:非理性的、煽动性的声音总是会比理智的、严谨的声音更加有效地发动群众。纵观历史,不管是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毛发动的文革,前些时候愈演愈烈的反日游行,还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五.四”运动、天南门学潮,都反复证明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但同时我又特别反感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分子成天把“民智未开”之类的鬼话放在嘴边,要知道一个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也许根本搞不清奥巴马和麦凯恩的养老保险计划之间的差别,也许仅仅是因为奥巴马的明星范儿才把选票给了他。
由悖论二倒推出悖论三: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需要韩寒、刘瑜、龙应台这类与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的知识分子。我见到一些同辈的学者用很刻薄的语言批评他们,这样的态度非常不讨人喜欢。因为一旦他们成了媒体人,他们的作品就进入Popular Culture的领域,与作家、导演、艺术家的作用一样,所以你无权要求他们的主张要经得起学理推敲。另一方面,学术上的东西如果不是同行根本就听不懂,怎么可能深入大众。网上点击高的什么郎咸平啊乔姆斯基啊,也只能蒙一蒙中国的大学生了。你见过真正做学问的人就知道了,他们根本没时间成天在媒体上走穴。
悖论一:在改变任何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感慨个人的渺小,希望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可凡是能够调动整个国家机器去高效率地完成一件事的政府,都不会做什么好事,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由悖论一倒推出悖论二:非理性的、煽动性的声音总是会比理智的、严谨的声音更加有效地发动群众。纵观历史,不管是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毛发动的文革,前些时候愈演愈烈的反日游行,还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五.四”运动、天南门学潮,都反复证明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但同时我又特别反感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分子成天把“民智未开”之类的鬼话放在嘴边,要知道一个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也许根本搞不清奥巴马和麦凯恩的养老保险计划之间的差别,也许仅仅是因为奥巴马的明星范儿才把选票给了他。
由悖论二倒推出悖论三: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需要韩寒、刘瑜、龙应台这类与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的知识分子。我见到一些同辈的学者用很刻薄的语言批评他们,这样的态度非常不讨人喜欢。因为一旦他们成了媒体人,他们的作品就进入Popular Culture的领域,与作家、导演、艺术家的作用一样,所以你无权要求他们的主张要经得起学理推敲。另一方面,学术上的东西如果不是同行根本就听不懂,怎么可能深入大众。网上点击高的什么郎咸平啊乔姆斯基啊,也只能蒙一蒙中国的大学生了。你见过真正做学问的人就知道了,他们根本没时间成天在媒体上走穴。
订阅:
评论 (Atom)